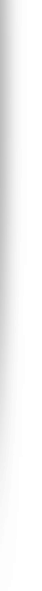作者:单建国
2006年6月19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的第十四号文件规定:自即日起暂停为登记地址为民用住宅的企业办照。这一文件规定的出台立即引起轩然大波,成为近期北京楼市的热点问题之一。十四号文件规定涉及到了居民、业主、租户、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等多方的切身利益,对此文件规定的观点态度也各不相同,拥护者有之,反对者有之,无奈者有之。
是否应当对住宅禁商?有无法律依据?十四号文件规定能否从根本上解决住宅商用的问题?对禁止住宅商用问题是否应当“一刀切”?为什么只是“暂停”办照?“暂停”到何时?等等,这一系列的话题,也是近期北京楼市的热门话题。
住宅商用的现状及弊端
多年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审查企业的注册登记申请材料时,未对以民用住宅作为公司注册登记地址的行为予以严格禁止,因此有大量公司都陆续合法登记注册在居民住宅楼内。正因如此,住宅商用之风愈演愈烈,据有关媒体报道,北京市有60%的公司开在居民住宅楼内,仅今年一季度,在朝阳区注册的公司就有60%以上的办公地点设在居民住宅楼内。
随着住宅商用的比例越来越高,其弊端和危害也越来越明显。首先,住宅商用扰乱了居民的正常生活。每天早晚是居民楼内电梯的使用高峰时段,此时,也正是居民楼内办公的员工上下班时间,他们的集体出入造成了电梯的拥挤,影响了居民正常使用电梯。白天有时赶上一些公司用电梯运货,居民们根本无法使用本应属于自己的电梯。工作日的白天应当是居民楼内十分清静的时间,但是,在楼内办公的人员以及前来联系业务的客户来来往往,再加上有的外来联系业务的人员乱按门禁系统、乱敲住户房门,有些公司的员工肆无忌惮地大声喧哗或者在午休时间打开超重低音的音响设备,有的公司员工在电梯间内打羽毛球,或者把楼道、电梯间当作吸烟室,聚众吸烟,混杂的人流、污浊的空气、嘈杂的噪声、拥挤的楼道和电梯,这一切把一个好端端的居民楼搅得乌烟瘴气,彻底地打乱了居民本应享有的一份安静。有的公司晚上加班到很晚、周末也加班,这样就造成居民在自己的住宅内正常的休息权利也被侵犯。居民的正常生活秩序被严重干扰和破坏,住宅的品质和生活的品质也随之大幅度降低。
其次,住宅商用侵犯了居民的财产权益。由于楼内办公人员、前来公司联系业务人员的频繁出入,以及搬运货物,加速了电梯等公用设施的正常损耗,缩短了这些设施的大修周期和使用寿命,增加了居民物业费用的支出,给居民造成了财产上的损失。
第三,住宅商用给物业管理带来困难,容易引发安全、治安、刑事案件。由于居民楼内办公司,一方面导致楼内的人流增加,且外来人员混杂,物业不好控制楼内人员的进出,很难有效管理。这就无形当中增加了楼内的消防、治安等安全隐患。有些人是到楼内公司办事,而有些闲杂人等则是打着到某公司办理业务的旗号混进楼内进行盗窃、抢劫。
从以上事实可见,住宅商用的泛滥,后患无穷,已经严重影响了广大居民的正常生活,因此,应当及时地予以禁止或加以限制。
第十四号文件产生的连锁反应
在十四号文件公布实施后,首先是造成了那些以住宅为登记地址、前去办理工商登记注册的人员被拒之门外,因为,按照该文件规定,自2006年6月19日起,暂停为登记地址为民用住宅的企业办照。其次是造成那些此前已经注册成立在住宅楼内办公的公司,无法再办理迁址到其他住宅楼内的注册地址变更登记手续。有的公司已经签订了住宅租赁合同并且交付了房租,但是却无法办理地址变更手续。更为尴尬的是,因为十四号文件发布得太突然,有的公司已经从原注册区县的工商登记机关办理了登记注册档案材料迁出手续,但是,因为十四号文件的出台,在新的办公地点却不能落户,有人形容这就像飞机起飞到达了目的地的上空却不能降落一样,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他们感到无奈。
因为长期以来一直未对住宅禁商,很多公司自成立时起就一直在住宅内办公,这是经工商登记部门核准的,现在这些公司能否在住宅内继续生存下去?明年能否顺利注册?这些问题在十四号文件中却找不到答案。这些公司对将来何去何从茫然不知所措。
由于根本不可能想到工商部门会突然出台这样的规定,有的公司甚至已经购买了居民住宅作为办公场所,准备在居民区内长期安营扎寨。十四号文件的出台,也彻底粉碎了他们的美梦,由于政策的变化,现在他们需要考虑的是已经购买的房屋如何处置?
住宅禁商可以逐步改善居民的居住环境,提升住宅品质,自然会受到很多居民的拍手称快,应当说受益者是大部分居民。但是,这一政策也并非对所有的业主都是利好的。
根据十四号文件,登记注册时凡提交《房屋所有权证》写明的房屋用途为住宅,购置商品房购房合同写明房屋用途为住宅(公寓、别墅)的,《房屋所有权证》和购房合同中房屋用途的表述无法辨别为住宅或商用的(商住、综合等),均不予登记注册。十四号文件实施之后,在业主这一群体中受影响最大的是那些商住楼、公寓和纯商务公寓楼的业主,也有人形容这一群体是“受伤最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最近这些年政府批准新建的商务公寓中,有些在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审定的设计图纸中根本就没有厨房,也没有煤气管道,而是按照纯商务用途设计的,这种房屋不具备居住条件,十四号文件对这样的房屋也予以禁商,那么,将来这类商品房作为商品的使用价值将如何体现呢?这些纯商务公寓都是由政府主管部门批准立项、审定设计方案和批准开工建设的,也是政府主管部门批准销售的,同样也是由政府主管部门颁发的《房屋所有权证》。这样的商务公寓在北京并不少见。十四号文件的规定对纯商务公寓也采取了“一刀切”的做法,显然根本没有考虑到这部分业主的利益,对纯商务公寓禁止商用,不仅于法无据,而且也不合情理。无法出租商用,又不能自己居住使用,每月还要还按揭贷款,这令很多商务公寓的业主一筹莫展。
由于纯商务公寓无法居住,十四号文件又规定不允许办公使用,自然会影响到物业公司收取高额的物业管理费,所以,十四号文件也会影响到物业管理部门的经营情况。由于购买纯商务公寓不能实现投资目的,肯定会降低投资者的购房欲望,对于正在建设销售当中的商务公寓的销售情况则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十四号文件的突然出台,现在还未实际解决住宅商用的扰民问题,但在客观上却造成了几家欢喜几家愁、众说纷纭的局面。
十四号文件对住宅禁商没有法律依据
在现行的法律法规当中,并没有禁止住宅商用的规定。正因如此,长期以来经工商登记机关核准成立了大量的以住宅为登记住所地的公司。目前,在法律法规没有修改的情况下,作为行政执法机关是否有权以自己制定的住宅禁商文件作为行政许可的审核条件和依据呢?笔者认为,虽然十四号文件有利于解决住宅商用所造成的扰民问题,其积极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从法律角度来说却是存在法律障碍的。
(一)十四号文件的规定与现行的法律法规的规定相悖
2003年8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该法于2004年7月1日起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4条规定: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范围、条件和程序。第12条规定:企业或其他组织的设立等可以设定行政许可。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可见,申请注册成立公司的行为实质上是在申请行政许可。第38条第1款规定: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申请设立公司应当提交公司住所证明。第24条规定:公司住所证明是指能够证明公司对其住所享有使用权的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71条规定: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根据这一规定,房屋所有权人有权将房屋出租获利,因此,承租人也有权通过签订租赁合同取得住宅房屋的使用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54条规定:住宅用房的租赁,应当执行国家和房屋所在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租赁政策。由此可见,国家法律中没有关于住宅禁商的规定,而北京市人民政府也没有制定关于住宅禁商的政策。
根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在申请公司登记时,如果申请人提交了有效的租赁合同,也就足以证明其取得了该房产的使用权,在现行的法律法规当中没有禁止住宅商用规定的情况下,如果申请人所提交的申请没有违反法律法规之处,工商登记机关作为行政许可的实施机关,就应当像以往一样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而没有任何理由不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根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可见,十四号文件中关于“登记注册时凡提交的《房屋所有权证》写明的房屋用途为住宅,购置商品房购房合同写明房屋用途为住宅(公寓、别墅)的,《房屋所有权证》和购房合同中房屋用途的表述无法辨别为住宅或商用的(如商住、综合等),均不予登记注册”的规定明显与现行的法律法规规定相悖。
(二)十四号文件没有法律依据
行政机关应当依法行政,同时,作为行政许可的实施机关也同样应当依法行使行政许可的审查批准的权利。十四号文件既不是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也不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制定的行政规章,而是由作为行政许可的具体实施机关的工商局自己制定的一个文件。这里就涉及到了一个行政许可的具体实施机关是法律法规的执行者还是制定者的问题,很显然,行政许可的具体的实施机关是行政执法机关而并非立法机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16条规定:法规、规章对行政许可条件作出的具体规定,不得增设违反上位法的其他条件。所以,十四号文件的出台实际上是行政许可的实施机关自行增加和提高了准予行政许可的条件,执法者自行制定了规则,扮演了立法者的角色。因此,北京市工商局作为行政许可的实施机关自行制定并提高准予行政许可的条件的行为,没有法律依据。
(三)在执行十四号文件的过程中将出现混乱和尴尬的局面
首先,根据该文件的规定根本不能彻底解决民宅商用的问题。因为在十四号文件下达之前,已经在住宅登记注册的企业不需要遵守该规定,至于明年企业年检时是否还允许继续在住宅里开办,还需要等待通知。这一系列不确定的因素和“暂停”二字,都不得不让人对十四号文件的效力和前景产生疑问。最关键的是,依据十四号文件根本不可能达到预期目的。
其次,在相关法律法规行政规章都没有任何修改变化、国家和地方的法律环境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十四号文件的公布实施,不仅造成了行政许可的实施机关在文件实施前后执行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审查批准标准的问题,同时还造成了在相同的法律环境下,与很多省市自治区的行政许可审查批准标准不一致的问题。这种情况的出现显然是一个法治社会的尴尬。
第三,对于在十四号文件下达之前已经在住宅登记注册的企业将来年检的问题,则是工商局自己为自己出了一道难题。这些企业在开业注册登记以及此前年检时,工商部门都已经许可他们在住宅楼内办公,如果今后工商部门以在住宅内办公为由不给予年检,那么显然是在自己否定自己,而且属于擅自撤销或变更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相反,如果今后继续给予年检,允许继续在居民住宅内经营,则与制定十四号文件的初衷再次背道而驰,不仅没有达到制定文件的目的,还会影响行政许可实施机关的威信和形象。
第四,北京市工商局曾经在200之年6月17日发布过《关于在居民楼内设立企业有关问题的通知》,该通知中明确规定:允许企业(或个体工商户)以居民楼中的居住用房屋作为住所(经营场所)从事科技开发、咨询服务、市场调研、企业形象策划、打字、复印、图文设计、动画制作和广告经营活动,在其登记注册过程中,不再要求提交居(家)委会、物业管理委员会等居民自治组织出具的证明文件。这个通知允许在住宅楼内开办科技开发等企业,4年时间之后,在法律环境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十四号文件则禁止开办一切企业,不仅前后自相矛盾,而且作为一项政策显然不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还会让人有朝令夕改的感觉。
治理住宅商用的问题需要完善的法律法规和时间
认为十四号文件没有法律依据,并不等于支持住宅商用。既然住宅商用的问题已经暴露出了诸多的弊端和危害,那么这一问题也就非解决好不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因此,解决住宅商用这一复杂的社会问题,首先要靠完善法律法规。
不可否认,现行的法律法规当中确实没有禁止住宅商用的规定,但是,现有的法律法规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是留有接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54条规定:住宅用房的租赁,应当执行国家和房屋所在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租赁政策。根据这一规定,北京市人民政府有权依法制定相应的住宅用房租赁政策,其中可以规定关于住宅禁商的具体措施。依据法律规定,北京市人民政府制定的住宅用房的租赁政策完全可以作为下属的行政许可的实施机关审核批准的依据。在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时,也应当增加对住宅商用问题的限制性规定。同时,在即将出台的物权法中也应当对住宅商用的问题作出限制性的规定。当然,不论制定政策还是法律,都不能抛开客观现实,都必须考虑到合理性和可行性。健全完善的法制才是确保彻底解决住宅商用的根本。
长期以来,工商登记机关一直没有严格禁止住宅商用,而且现在已经有大量的公司经工商部门审核批准、合法地登记注册在住宅楼内,这是不容忽视的客观现实。一夜之间,靠一份文件就能彻底改变法律环境、扭转观念、解决住宅商用的问题,显然是不可能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住宅商用的问题之所以发展到今天的局面,不是短时间内形成的,涉及到的也绝不是少数人和少数公司的利益,因此,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靠简单的行政手段就能将问题彻底解决。
解决住宅商用这一复杂的社会问题,必须要注意区别不同情况,决不能搞简单的“一刀切”。笔者认为,对于普通住宅楼应当明令禁止商用,对这种住宅楼内的公司要逐步予以彻底清除,还居民一个安静舒适的居住环境,但是,也不能不考虑那些在住宅内办公的公司的实际情况,而是要制定一个合理的时间表,给那些公司一定的迁址准备时间;对于一般的商住楼、公寓楼的商用问题则应区别对待,应当根据具体情况,有条件地加以限制,而不应绝对禁止其商用;对于那些不具备居住条件的纯商务公寓的商用问题,则根本不应予以禁止,而是应当明确允许作为商用。
政策和法律要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同时还要体现人性化和合理性。制定住宅禁商的政策和法律,既要有效地解决住宅商用的问题,也要兼顾到各方的利益。这样既能体现政府之威信和法制之尊严,又能够使法律、政策得到认真的贯彻实施,收到实效,从而进一步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和稳定。此文发表在《北京律师》2006年第4期。